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思维导图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法治国家公民诉讼权宪法化和国际化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了公民诉讼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人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诉讼和司法制度之设计与改革应对公民诉讼权予以关注。文章对诉讼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初步界定,并探讨了公民诉讼权宪法和司法保障的具体机制。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 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 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 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 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85e005bed629ba5fe045f9039025f4a2
思维导图大纲
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关 键 词】诉讼权/宪法保障/司法保障
在20世纪的世界法治发展史上,一个应该受到关注却并未获得中国学者充分注意的现象是公民诉讼权的确立与发展。综观法治发达国家之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公民诉讼权为不少国家关注与保护,构成多国司法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
显然,对于这样一项具有普适性的权利及相应之运作实践,中国学者没有理由予以忽视,尤其就中国司法改革的进路而言,不管司法程序打造如何,如果公民无法迅速、有效地行使诉讼权,那么,立法者和法学家的诸多努力都将枉费。有鉴于此,探讨公民诉讼权的有关问题并以此评价中国司法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而研究改革之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诉讼权——公民的基本权利
所谓诉讼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即司法保护请求权。具体而言,公民诉讼权表现为各种类型诉讼中的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等。总而言之,凡属要求启动或参加司法救济程序进行裁判之权利,均属公民诉讼权。
对公民的诉讼权,多国宪法和国际法律文件均自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尽管在翻译和讨论时有不同的表述和话语,如“接受裁判权”、“接近法院的权利”(注: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律师之任务》,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86页。)、“接受法院审判权”(注: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公正审判请求权”和“程序保障请求权”(注: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有的则简单化为“起诉权”(注:说其简单化,是因为这一界定忽略了上诉权、再审请求权及作为被告的公民之应诉权、反诉权等启动或参加司法程序的权利。),但整体来看,采用“诉讼权”这一表述较为科学、简洁,表明了这一权利的核心和实质内容——公民要求启动诉讼程序、参加诉讼程序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诉讼权与公民的社会生活、法律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存在于各个诉讼领域中。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宪法诉讼、刑事诉讼都存在着对公民诉讼权的保障和落实问题。
在民事诉讼领域,公民诉讼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发生了民事纠纷,在文明社会禁止私力救济的状况下,如果公民要求启动司法程序、参加诉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就谈不上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公民权益的维护。所以,在民事诉讼中公民享有诉讼权就理所当然。在此领域,公民诉讼权的主要内容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均得以全面体现。需要指出,公民诉讼权与学术界纠缠不清已长达两世纪的诉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厘清。应当明确:诉权仅存于民事诉讼中,而公民的诉讼权存在于各个诉讼领域中;诉权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前苏联、日本学界学理讨论的权利,而公民的诉讼权是法定权利,也为许多国家公民实际享有。(注:诉权自19世纪前半期由德国学者提出后,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争论不休。私权诉权说认为诉权或是民事权利的“发展阶段”、“组成部分”或是民事权利的“强制属性”;抽象诉权说的提出揭示了诉权的公权属性,同时导致了程序权同实体权的分离、诉讼法同实体法的分离;具体诉权说认为诉权是要求法院依据实体权利作出有利判决的权利;而前苏联学者提出的二元诉权说认为诉权包括程序意义诉权和实体意义的诉权,前者指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后者指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实现其实体权利的权利。上述各种诉权学说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诉权是一元的、程序意义的,应仅局限于民事领域进行讨论,以免与公民诉讼权这一宪法权利相混淆,带来认识和研究上的混乱。)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损害时,也享有寻求司法救济、得到法院保护的权利。因之,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享有和行使诉讼权以接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要指出,这种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纠纷解决问题,更是公民借此对抗行政权力滥用及膨胀之问题。在此领域,公民享有的诉讼权以起诉权、应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为表现形态。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诉讼的发动权大都收归于国家的公诉机关,但诉讼权同样存在。首先,自被害人的角度分析,被害人除了有申诉、控告、检举这样一些间接发动审判程序、要求司法保护的权利外,还享有刑事自诉程序中的自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及参与刑事审判的权利。其次,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角度,获得国家法定的审判机关审判应视为其享有的重要权利。另外,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还享有应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在自诉程序中还享有反诉权,这些权利无疑也是公民使用司法制度、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二、公民诉讼权的宪法化与国际化——对法治国家的考察
考察法治国家的宪政史可知,各国宪法均对公民诉讼权予以明文规定。在英国,1215年《大宪章》中正当程序条款已包含了保障公民请求国家开展一定诉讼程序以解决纠纷的权利以及要求攻击防御权利之精神。(注:陈刚为《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民事诉讼》所作评译,第3页,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时至今日英国虽无成文宪法,但实际上一直承认公民的诉讼权。
在大陆法系诸国中,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任何人皆享有不可剥夺的去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意大利1946年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自由地向法院提起诉讼。”联邦德国1948年12月27日《德意志人民基本权利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如权利遭受公共机构侵犯,任何人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德意志人民基本权利法》第103条第1款亦明文保障任何人有请求法院裁判的权利,即诉讼权。
除上述国家外,将公民诉讼权规定于宪法的国家众多,诸如:巴西宪法第153条第4款、墨西哥宪法第17条、荷兰宪法第167条、西班牙宪法第24条、希腊宪法第20条第1款、土耳其宪法第36条、前苏联宪法第57、58条。
需要指出,诉讼权的内容是发展的。日本学者杉原泰雄在以比较法学视角考察宪法的历史时讲道“现代市民宪法,就自由权、受益权之类的传统性人权,不仅继承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的解释,而且把它在扩充、加强”。(注: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他认为受益权,在近现代立宪主义市民宪法中包括有受裁判的权利、损失补偿请求权、请愿权。同时,杉原泰雄又指出:“作为受裁判权的一环……有一种倾向即允许就立法及其它国家行为是否合宪问题请求法院裁判”。(注: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因此,综合多国的宪法发展史来看,公民诉讼权不仅在近代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而且在现代市民宪法中有了进一步的强化,领域也有所扩充,包括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
三、赋予公民诉讼权的法理基础
确立公民诉讼权且赋予其重要地位,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
首先,这与纠纷解决权力的国家化及司法机关的运作方式——不告不理直接相关。在人类生活早期,纠纷的解决依赖于氏族组织用共同体内部的道德或习惯进行公共裁决或纠纷双方的暴力争斗。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纠纷成为普遍现象,威胁着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因此,国家开始干预社会成员的纠纷,以第三者的身份解决纠纷,用国家力量取代“私力救济”。这样,国家就有了进行“公力救济”以解决争端的职责,与此相应,公民也就产生了要求国家裁判的权利及对其参与裁判权进行保障之权利。对此,近现代思想家关于国家作用的论述可以印证,例如,德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威廉·冯·洪堡在其1792年所著的《论国家的作用》中强调:“国家最优先的义务之一就是调查和裁决公民权利的争端”“在社会里,公民安全主要赖以为基础的东西,就是把整个个人随意谋求权利的事务转让给国家。但对于国家来说,从这种转让中产生了义务,……因此,如果公民之间有争端,国家就有义务对权利进行裁决,并且在占有权利上要保护拥有权利的一方。”(注: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的“公力救济”在前期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国家注重强力裁判和社会稳定的维护,并不特别关注冲突主体的权益保护。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想、法治思想的发展和弘扬,国家的公力救济才有了维护冲突主体权益、保障公民要求司法救济权利的根本性质。因此,公民使用司法制度、维护权益的要求是一种权利,与之对应,国家的裁判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国家赐与公民的恩惠。
不仅如此,现代审判机关虽有纷纷解决的职责却无主动干预的职权,必须保持审判的中立性,恪守“不告不理”原则。这样,审判权本身不具有主动保护公民权利之运作方式,它与公民的权益之间还隔着一道横沟,需要架设桥梁。诉讼权便是连接公民权益与审判权间的中介,它将公民的争议引到了司法权面前,使司法审判得以启动。所以说,缺失了公民的诉讼权,公民就失了寻求司法保护和纠纷解决的手段,审判权力也就无从启动与运作。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成员的权利遭受侵犯后不能得到恢复,往往肇始于诉讼权受限、无法接近法院、进入司法程序,其次才是由于审判不公正、公民诉讼权利被弱化和剥夺。典型的莫如英国的令状体制。自12世纪亨利一世在位后长达几世纪的英国,如果社会成员权利被侵害,欲自王室法院获得救济,完全要看他能否得一纸加盖君主名衔的指示法院之执达员命令被告出庭并就原告起诉提出答辩的令状。因此,“在令状体制下,若欲求得法院之救济,则原告有义务选择适当之诉讼方式。否则,王室法院将不给予任何救济,如诉讼方式选择不当,则无救济可言。甚至不许再行起诉”。“在这种情况下之权利存在,取决于法院救济之存在;而法院救济之存在,又取决于此一令状之存在”。(注: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361页。)
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限制老幼残疾及妇女起诉权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不得轻易越级上诉制度以及明清时期最为典型的起诉须在“放告”日、严惩讼师的规定、严格的状纸制度也都限制了平民的诉讼权。(注: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31、63、86、189页;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间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398页。)
由此,公民的诉讼权就显得相当重要,虽然启蒙思想家们在提出人权时,未将诉讼权列入人权的基本内容中,但随着人类在法治道路上的探索,法治国家、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公民的这一权利,通过宪法和国际文件将其上升为宪法权利,列入了基本人权。莫纪宏指出,“相对于政府的保障责任而言,唯一可以从平等性和穷尽性来保障法律上人权的实际性的只有诉权……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第一制度性人权。”(注:这里的诉权实际上并不是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而是本文提出的诉讼权,参见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通过上文对法治国家宪权史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诉讼权这一保障公民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安全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程序权利本身成为了公民的基本人权。
不仅如此,在法治社会,一切社会关系以及权力的设置与运作都应受法的支配,而“国民是形成法的主体,是促进法前进的原动力,而不仅仅是被统治的客体”。(注:邱联恭:《司法现代化与律师之任务》,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255页。)为人保证公民法的主体地位,理应赋予公民诉讼权,开放司法制度,使公民平等、充分地接近法院,参与法的运作。缺失了诉讼权,公民法的主体地位将难以充分体现,也必将在权力的肆意横行和压迫下淡化和削弱。
四、引人注目的司法改革新动向——法治国家的接近正义运动
诚如上文所言,如果公民的诉讼权不能得到周全、充分的保障,则其本应享有的程序权利及实体权利将有名无实,公民作为法的主体地位不能得到保障,因此,自诉讼制度内及诉讼制度外两方面保障公民的诉讼权,使其能够接近法院,享用司法制度,就成为法治国家之法治建设不能不关注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的70年代“在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卡佩莱蒂的倡导下,提出了各国政府都有义务保护当事人的接受裁判权,为当事人从实质上实现接受裁判权提供应有的保障及扫清障碍的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一场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接近正义的运动”。(注:见刘俊祥为《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所作序言,第4页,载莫诺·卡佩莱蒂等:《福利画家与接近正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这场接近正义运动最鲜明的特点是制定立法、司法及相关制度改革计划,并向各国“政策决定者”提供“政策意向性结论”。而一些国家也自“福利国家”之立场,积极地担负起保障公民诉讼权,使其能实效地使用司法制度的使命。
由此,相当多的法治国家对司法及相关制度进行了深入改革,健全、落实了一系列的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改革及相应举措不仅在观念上、法律规定上,更重要的是在公民诉讼权的切实享有上起了积极的建设作用。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分析的:“新型的正义以对有效性的探索为标志——有效的起诉权和应诉权,有效接近法院之权利,当事人双方实质性平等,将这种新的正义引入所有人可及的范围。”(注: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大致而言:这一运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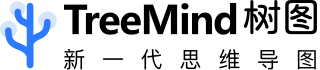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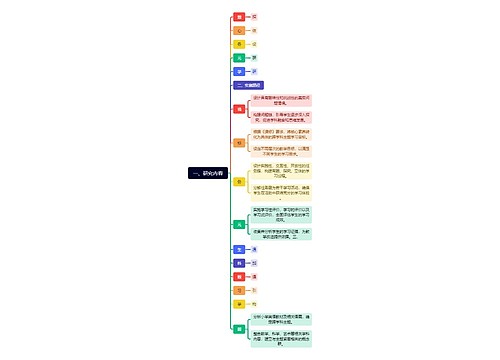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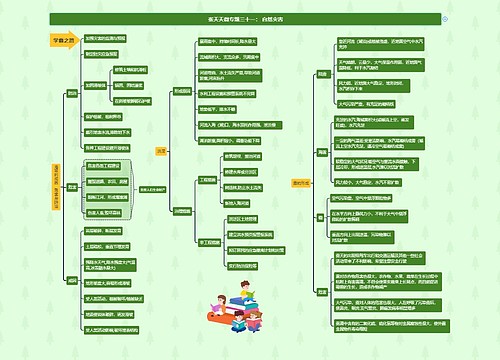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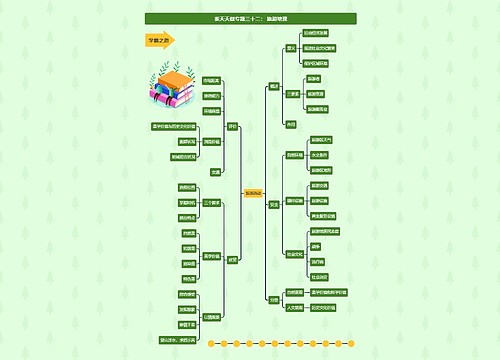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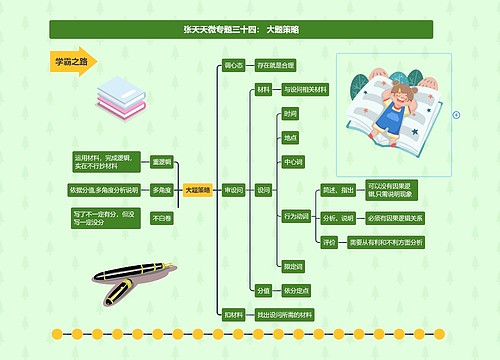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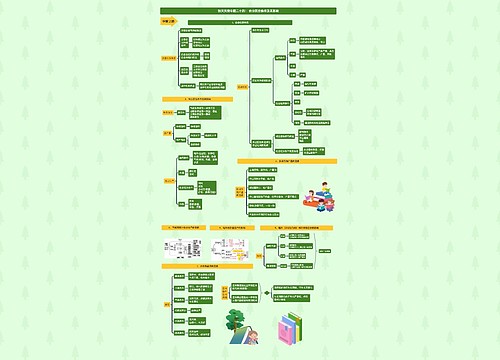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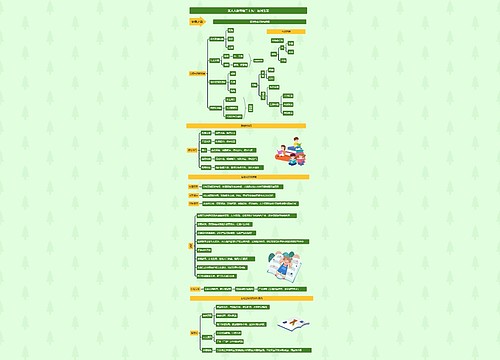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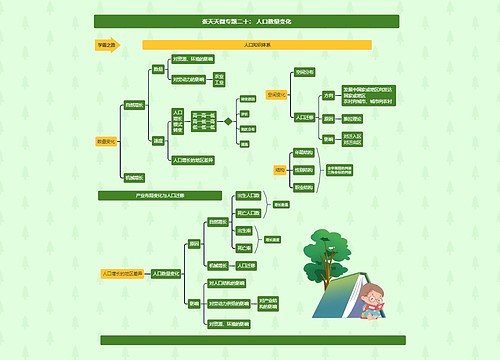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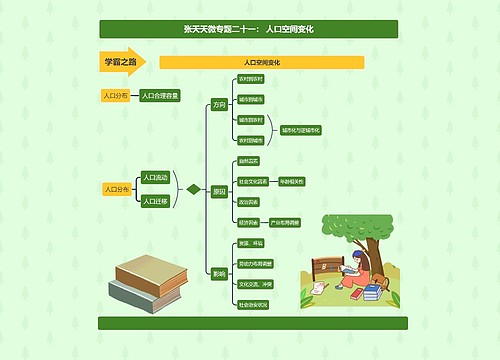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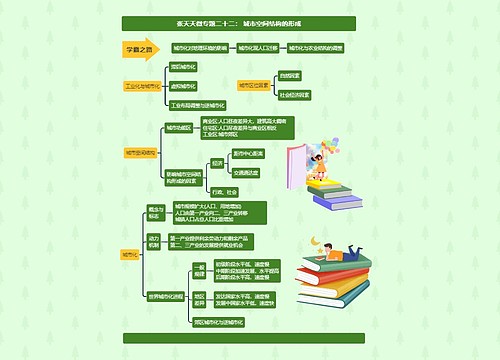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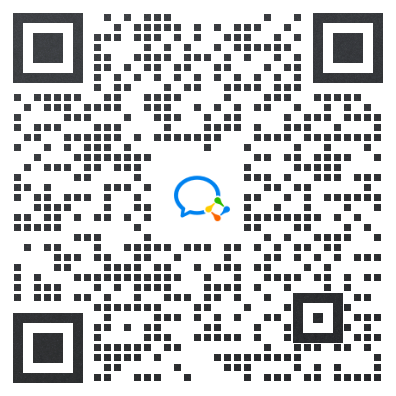
 上海工商
上海工商